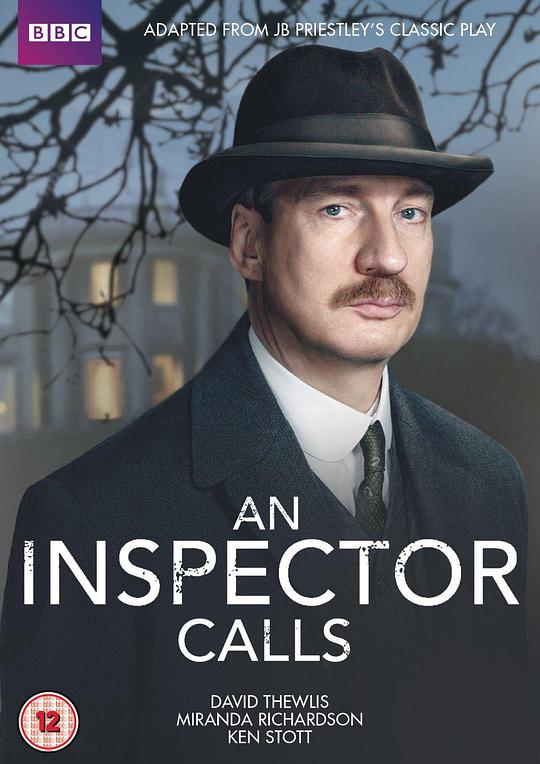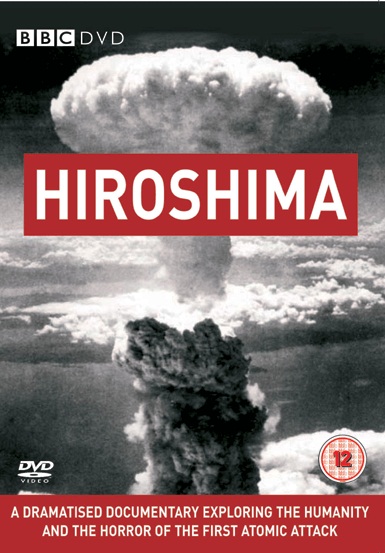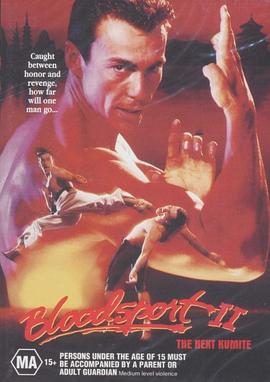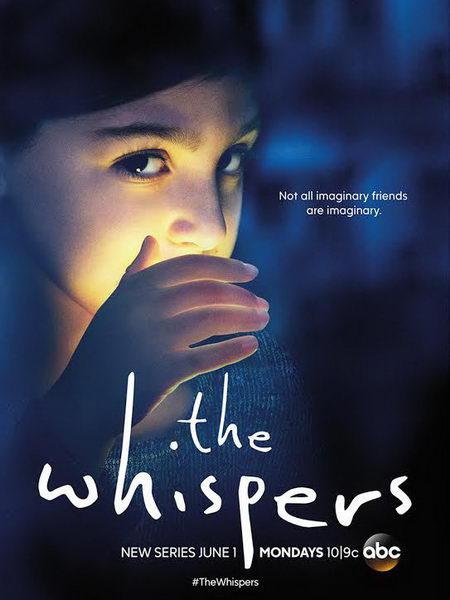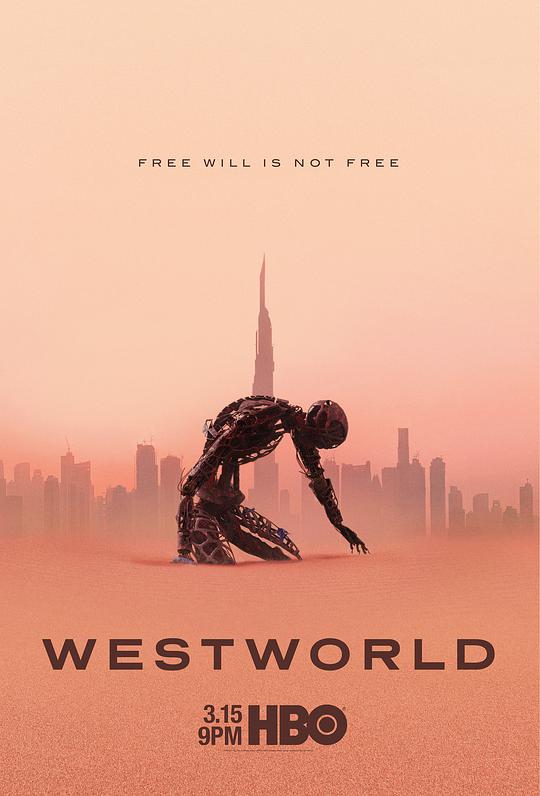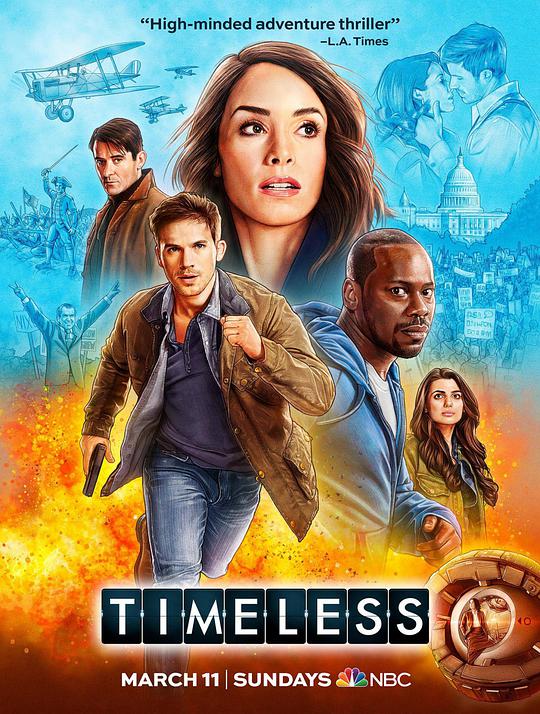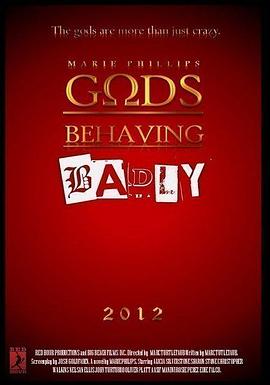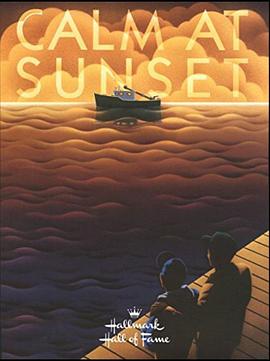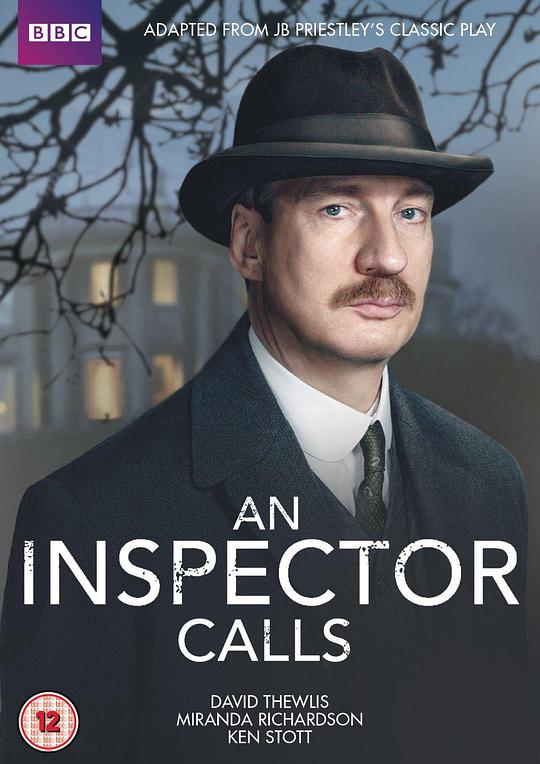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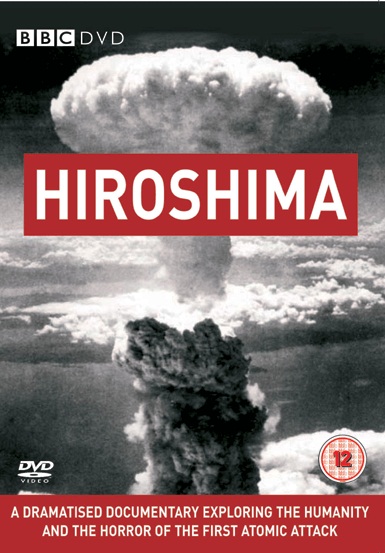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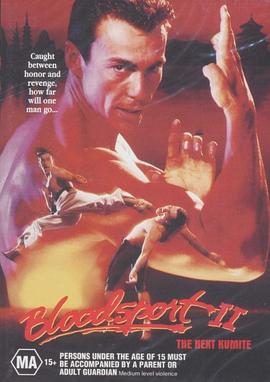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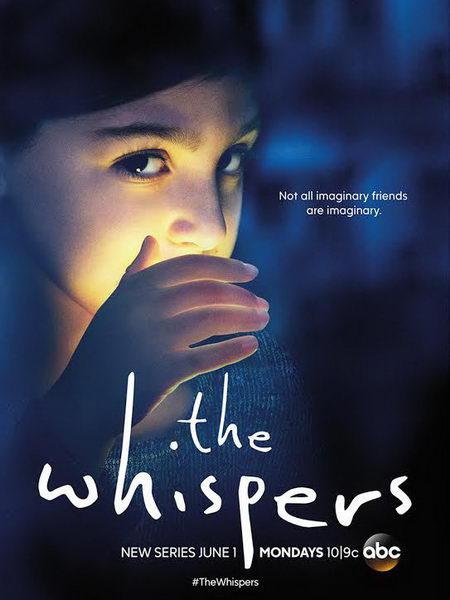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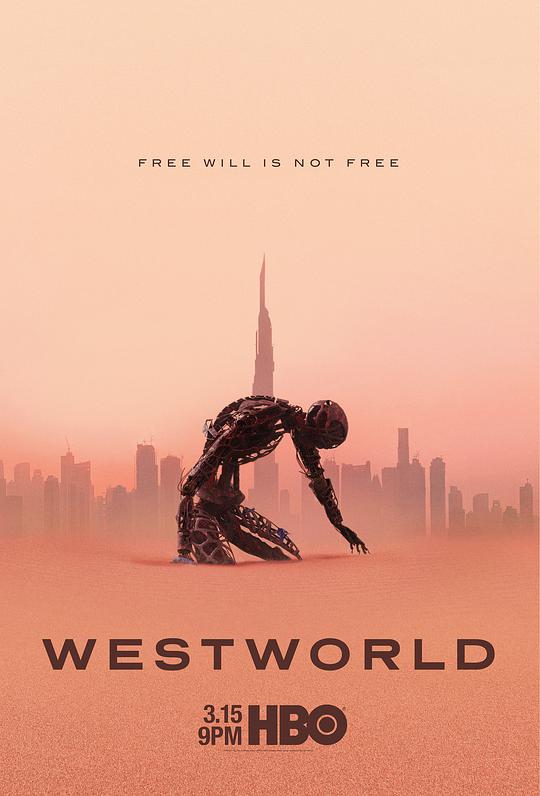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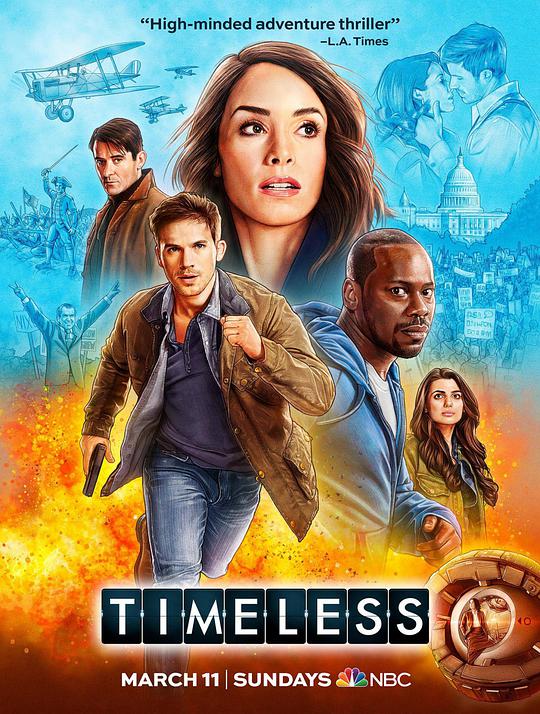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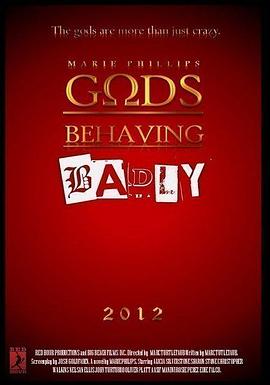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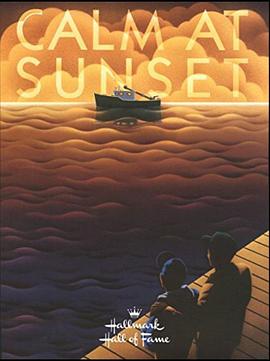


1984年7月7日,一个闷热的夏夜。缅因州班戈市,肯杜斯基河上的州街大桥。
23岁的查理·霍华德刚从一家酒吧出来,和朋友走在回家的路上。三个少年拦住了他们。没有太多言语,拳头落下来,球鞋踢过来,查理被拖到桥栏边。他挣扎着喊叫,说自己不会游泳。少年们笑了。然后,他们像扔掉一袋垃圾一样,把他扔了下去。
查理·霍华德的尸体在第二天早晨被发现,卡在河中央的一块岩石上。他的罪过只有一条:身为同性恋。
这起谋杀案震动了班戈,却没有震动太久。几个月后,生活恢复如常。桥上依然有情侣散步,河水依然平静流淌。
只有一个人无法释怀:住在班戈的恐怖小说家斯蒂芬·金。两年后,他出版了一本一千多页的长篇小说《它》(IT)。
《小丑回魂》影视作品的原著:《IT》
书中,他虚构了一座名叫“德里”的小镇,几乎是班戈的翻版。而查理·霍华德的死,被他写成了一个叫阿德里安·梅伦的角色——同样在嘉年华之夜被殴打,同样被扔下桥,同样溺亡在那条穿城而过的河流里。
同样,在德里,比起鲜血,人们更厌恶那些擦不掉的血迹。
今年年底,《小丑回魂》前传剧集《欢迎来到德里镇》上线。它以更具象化的方式,为观众呈现德里的面子和里子。
从外表看,德里简直是美式现代小镇的样板间:商业兴旺,街道整洁,甚至有一种近乎凝固的安稳。
然而,当你走入德里,很快就会发现居民们令人不适的“精神特质”:对于镇上的暴力,他们总是冷眼旁观。即便发生大规模惨案,居民们也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忘记它。
在德里镇的街道上,电线杆和布告栏总是显得格外臃肿,上面层层叠叠地张贴着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。然而,路过的行人们早已对上面的面孔熟视无睹。那些印着“MISSING”的传单只能在风中剥落、变色。
人们步履匆匆,眼神从那些失落的灵魂上滑过,不留一丝波澜。仿佛承认失踪的存在,就会刺破他们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安稳假象。他们不是没看见,而是选择不记得。他们用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,把死者埋进记忆的最深处,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向明天。
然而,一旦布告栏上贴出带有数字的悬赏公告或招商传单,人群却会瞬间聚集,争相传阅。
德里人就是这样,对失踪的儿童不闻不问,却可以为了几百美元的悬赏拿起猎枪,以暴力谋求小利。
这座虚构的缅因州小镇,本该与我相处不同的平行空间。可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。
不是似曾相识,而是过于熟悉。
剧中有一个原创角色,空军将军弗朗西斯·肖。当他用统计学家的口吻淡淡说出“德里镇每年失踪的儿童,其实远少于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”时,我忽然明白了那种熟悉感从何而来。
这句话我听过太多遍了。不是原话,而是那种语气。
那种把鲜血折算成百分比的冷静,那种用“大局”碾压个体的理直气壮。
德里镇不在任何地图上。但它存在于每一个学会了沉默的地方,存在于每一双及时移开的眼睛里,存在于每一句“别添乱”和“向前看”之中。
1.黑色基石:
一部被抹除的“鲜血地方志”
小说中,迈克·汉隆——"失败者俱乐部"里唯一留守德里的成员,以图书馆员的身份守护着这座小镇的黑暗记忆。
《小丑回魂2》中的迈克·汉隆
他用大半生的时间记录下一部《德里:一部城市野史》,一摞未曾出版的笔记与零散手稿,堆满剪报、老照片和口述记录。
翻开它,你会发现那是一部由火灾、失踪和屠杀编织成的黑暗编年史。
1906年复活节,基奇纳钢铁厂爆炸案。 数百名儿童在寻蛋游戏中被炸飞。日落前,救援人员拖出七十二具尸体,最终一百零二人罹难。爆炸从未得到解释,因为四座熔炉当时全部关闭。
剧集的开场动画展现了这场爆炸案
1929年,布拉德利帮枪杀案。 官方记录称这是“警方英勇激战黑帮”,但真相是七名匪徒被一群“德里的好居民”乱枪处决。事后,全镇两万居民中,愿意承认自己当天在场的不满十人。
1930年,“黑点”酒吧大火(在剧集中被改编为60年代)。 “缅因白礼军团”在一个深夜点燃了这家黑人士兵俱乐部并堵死出口,六十人丧生。这场惨案可谓惨绝人寰,充斥暴力和冤屈,但德里居民的反应把他们的集体精神属性展现得十分赤裸:
许多德里居民选择遗忘,不是说自己出城造访亲戚,就是那天下午在打盹,直到晚上听广播新闻才晓得出事了,甚至当着你的面说谎,假装没这回事儿。
镇上的种族仇恨,直接滋养了潘尼怀斯
可是在德里的官方叙事里,这些惨剧被轻描淡写地处理成“意外”,甚至被集体抹除,构成了德里镇的正确历史记忆。
那里的成年人们默契地配合这种需要。谈起这些灾难时,他们的语气里充满了一种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”的伪善觉悟。他们认为,翻动这些焦黑的废墟是不识大体的,会破坏小镇作为"宜居典范"的尊严。
这就是德里,拥有一种惊人的"觉悟":那些被拖入下水道的孩子,那些在大火中尖叫的黑人士兵,那些在节日里被炸成碎片的身体——它们都是维持繁荣所必须付出的、微不足道的代价。
人们不恨丑恶,不恨不公,只恨它们引发的响动惊扰了他们的美梦。
一旦响动化作文字、视频或求救信号闯入他们的视野,他们就会感到极大的愤怒,并渴望乃至主动要求受害者闭嘴。
在现实世界里,德里镇的这种"觉悟",有时会以一种近乎天真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贾樟柯曾带着《海上传奇》参加海外影展,一位留学生在映后质问他:"你为什么要拍这些?这会影响外界对我们的投资信心吗?"
在这种质问里,仿佛记录才是问题,而被记录的苦难只是一个需要被妥善管理的公关危机。
这样的人从未去过德里,但仿佛来自德里。
常有人为这种集体性的冷漠辩护:
在不可抗力的威逼利诱之下,选择沉默甚至与其合作,是基于生存本能的"合理"行为,应当被"理解"。
但,既然一个人享受了与强权合作的好处,既然这种"合理"的妥协侵蚀着大众的道德标准,甚至带来实质性的伤害,他就应当承受一定程度的指责。
德里的繁荣不是因为上帝眷顾,而是因为那里的居民与怪物达成了一种默契的‘交易’:以他人的血,换取我的安稳。”
但居民们不能一方面拿着这份"血酬"安享太平,另一方面又要求大众只能对其妥协报以同情。
2.上位者的需要:
当悲剧被精算为"秩序"
德里镇居民的沉默、麻木和遗忘,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道德缺陷。
然而,在喜欢秩序与稳定,厌恶变革与冲突的人眼里,这却是一种迷人的美德。
心怀野心的邪神死光(潘尼怀斯背后的黑暗力量),以及把稳定看作是极致之美的弄权者,怎能不爱上德里。
剧集里展现了潘尼怀斯的本体:Deadlights
《欢迎来到德里镇》里的空军将军弗朗西斯·肖,就是这样的弄权者。
他童年时曾在德里遭遇过死光的猎杀,侥幸逃脱。按常理,这样的经历应该让他对这个怪物恨之入骨。
但肖将军不是常人。
成为军队高层之后,他目睹了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种种"乱象":黑人民权运动、女性平权运动、反战示威……
在他看来,这些"内部混乱"比苏联这个外部敌人更加可怕。它们动摇根基,制造分裂,让国家失去凝聚力。
找回对德里镇的记忆后,他发觉此地独有的“魅力”:无论经历多少灾难,都能迅速恢复平静。
哪怕是发生了黑点酒吧纵火案这样的人间惨剧后,居民们也不追问,不抗议,不要求真相。他们只是安静地埋葬死者,修复房屋,然后继续过日子。
多么理想的社会模型!多么完美的顺从!
于是,肖将军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:他要凭借军队的力量,焚毁束缚死星活动范围的圣柱,释放潘尼怀斯,把整个美国都变成德里。
他自以为的理性,实际上是对“完美秩序”的贪婪。
当汉隆替那些失踪的孩子质问他时,肖将军的回答冷静得令人胆寒。既然社会能够接受汽车作为文明代价所带来的死亡,为什么不能接受一只怪物作为秩序代价所带来的"损耗"?
这就是宏大统计学的魔力。它可以把尖叫变成数字,把鲜血变成百分比,把一个个有名有姓的孩子变成报表上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。肖将军最阴险的地方在于,他不仅杀人,他还要通过合法化这种‘损耗’,让每个活着的德里人都在潜意识里成为怪物的同谋。
在肖将军的"格林计划"里,恐惧将被包装成必要的代价,人们将被训练得像接受车祸一样接受邻居小孩的失踪。没有抗争,没有追问,只有对秩序的臣服。
这种被恐惧驯化出的寂静,才是肖将军理想中的太平盛世。
而那些社会运动里,为追求公正而发出的呐喊,试图赋予每个“数字”以人的尊严,则是这种“盛世”的杂音,障碍。
所以你看,强权和德里镇居民,是天然的盟友。
3.从未剧终:
正在全球加速蔓延的“德里病症”
今天,人类依然生活在无数个“德里镇”里。
当人们面对一场火灾,第一反应是“不要发这种东西,影响心情”时;当人们习惯了对他人的困顿视而不见,只为了保住那份虚假的安全感时,每个人其实都在为潘尼怀斯喂食。
这种对“体面”的病态追求,或许可以让街道越来越干净,楼宇越来越宏伟,但人心底里的那个下水道,却越来越拥挤。
历史早已证明:那些被刻意遗忘的鲜血,最终都会倒灌回幸存者的客厅。这种"倒灌"并非文学虚构,而是文明运行的铁律:
1938年,英法牺牲捷克主权以求“一代人的和平”,次年二战全面爆发,曾经闭眼观望的伦敦与巴黎,无数楼宇被纳粹的炮火夷为废墟。
1994年,全球对卢旺达大屠杀的“不干预”,不仅留下了波及至今的难民危机,更直接点燃了席卷整个中非的大规模战乱,冲击了全球地缘安全。
1986年,切尔诺贝利事故初期,苏联当权者为了维持“社会信心”,在辐射尘早已笼罩城市时,依然坚持举行盛大的基辅五一节大游行。这种用隐瞒交换而来的“稳定”,最终化作无孔不入的剧毒微尘,倒灌进自以为处于“安全区”的普通家庭。
可悲的是,如同德里镇曾经每隔27年定会上演的血祭一样,历史的悲剧依然持续改头换面,在现实中循环往复。
正如特朗普将“1月6日”的国会山暴行重塑为“爱之日”,试图通过美化暴力来漂白集体的血腥记忆;又如声称“毫不关心乌克兰”的万斯,试图以远方焦土换取本土的“绝对秩序”。
这种选择性闭眼,旨在杜绝一切干扰“大局”的杂音,不就是在别处的废墟之上,构筑起令人窒息的太平吗?
当更多人习惯了用"地缘政治的复杂性"为远方的侵略辩护,学会了用"这不关我们的事"来关闭新闻推送,这实际上是在默许一种野蛮逻辑的复活:只要受害者不是自己,只要统计数字足够抽象,他人的牺牲就可以被重新命名为"必要的代价"。
加沙的瓦砾如此,乌克兰的焦土如此,德里镇下水道里的孩子亦如此。你今天允许别人的家园变成废墟、变成规则的真空地带,就是在亲手拆除自己客厅的防盗门。
当我们对言论空间的日益逼仄感到麻木,甚至嘲笑那些记录苦难的人是"负能量"时,我们实际上是在亲手拆除自家客厅的烟雾感应器。当火光映红窗帘的那一刻,任何沉默都将转化为致命的窒息。
潘尼怀斯和肖将军们最希望看到的,正是这种"极致的寂静"。
在这种寂静里,每个人都自以为安全,每个人都学会了"向前看",而身后的尸体则被悄悄折算成可接受的百分比。
肖将军和潘尼怀斯野心的实现,并不需要所有人都是直接做坏事的坏人。他们只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一个“想过安稳日子”的普通人,一个“识大体”的居民,不要理会他人的哭泣,只需低头赞美街道的整洁。
在《小丑回魂》的故事里,“失败者俱乐部”最终可以凭借勇气、友谊以及那份拒绝遗忘的记忆,深入黑暗的下水道,用古老的仪式封印那团吞噬灵魂的“死光”。
文学和影视给予了我们一种复仇的快感和获胜的幻觉,邪恶终会伏诛。
可现实中呢?
当“德里”不再是一座具体的城镇,而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瘟疫;当“死光”不再是虚幻的超自然力量,而化作了报表上冰冷的小数点,被美化的暴行叙事以及那些被拆除的烟雾感应器时,我们又能去哪里寻找那场足以终结黑暗的仪式?
祝我们好运。
THE END